华胥引(全二册)
Authors: 唐七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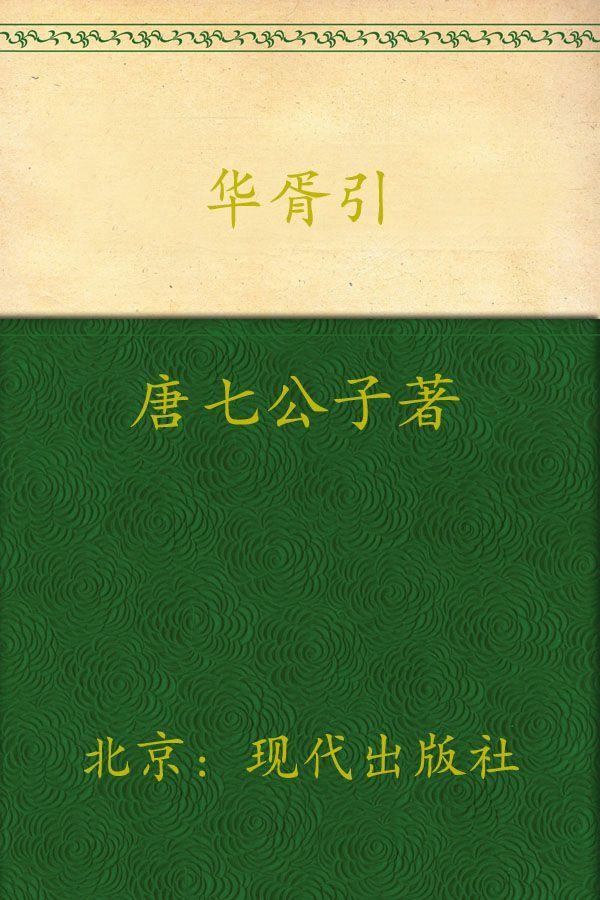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胥引/唐七公子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1.1
ISBN 978-7-80244-391-4
Ⅰ.①华… Ⅱ.①唐…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宇(2010)第228295号
华胥引
著 者:唐七公子
责任编辑:张晶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l
网 址: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印 刷: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27.5
字 数:400千
版 次:2011年1月第l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44-391-4
定 价:3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一、殉国的公主
二、国破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番外 决别曲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番外・棋子戏
文/方文山
“九州”此一称谓为古代中国的地理行政区总称,天下共分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凉州、雍州、豫州),九州大地即指中国大地,九夷来朝,万民咸服。
而于《列子・黄帝》的记载中,黄帝忧于国家动乱,遂“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于梦中见到了自己的理想之国,等醒来便以此治国,海清河晏,天下大治。而后黄帝以梦中所见,谱成一曲,即名《华胥引》,传说若三段齐奏,则颠倒迷离,见众生万象,偿一切所愿――唐七公子此书,此名大概便出典于此。
由此可见,唐七公子卓越的想象力之下,所依托的并不是凭空捏造想象,而是极其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这是现今作者们大部分都缺乏,但是于写作上很重要乃至于必需的专业素养。
书中之章节段落的引名如国破、浮生尽、一世安等,都精炼而颇具想象力,几乎都可以成为一个歌名来发挥,由此延展出具备中国古风的歌曲。还有其描景写物之用字遣词如画笔,时而如羊毫软宣,勾写婉约旖旎,哀感顽艳不可方物,时而是狼毫重墨,写家国历史浓墨重彩。一行一段的每一个描绘都极具画面感,再加上角色塑造之传神,勾勒人物性情之逼真,故事情节之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让读者几乎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本书,而是在看一场纸面上的电影,使读者在文字阅读行进间,仿佛观看了一幕幕影像化的历史剧。对我来说《华胥引》是会摆放在书桌上台灯边的一本小说,会在看完之后一次次地信手翻来,随意展开一页,都是一场影像化的文字!
文/许常德
或许,只有透过死的过程,才能找到生的意义。
或许,历史就是需要从时间流逝中才能找到拥有的价值。
在2012末日传说前,唐七公子的《华胥引》给了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新生的机会,女主角从死亡开始,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牵引出一段一段玄妙的故事,借着一个叫华胥引,可以让人梦想成真的秘术,女主角由此而展开了她的冒险!
华胥引弹起的时候,弹奏者和祈愿者就会一起沉入秘术编织成的梦境中。
梦境里误会可以解释,错误可以挽回,想说的话终于能说出来,想要的邂逅可以不必错过,于是皆大欢喜人人幸福,代价是一条命,从此沉溺在那个幸福的梦里。
换了是你你要不要?
你有没有什么错误要拿生命去换?
没有的话,恭喜你,不犯错,不伤人不伤己。
有的话也恭喜你,并不是谁都会犯拿生命去换的错。也不是犯了错的人都想拿生命去换,肯去换,还有救。
也或许不要以自身利益的角度,人才会公道地看待世事,这本书,要你经历的就是放下自我,拥抱全新的可能。
文/姚谦
我很少为人写序,因为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在文学创作里,我只不过是一个阅读者和小学生,在我眼里能写出一篇感人的文章和故事都是一件非凡的成就,我羡慕有这样才华与能力的人,我很乐意被他们引导入一篇一篇动人的故事与文章里,如果要我说出读后感,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着,但是要我写序,那就太为难我了。但是这回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计划着退休后开始多写一些文字,而结识了一些出版社,因此有机缘抢先看到唐七公子的新作《华胥引》,因为在别人之前阅读了,所以也忍不住先说了阅读心得。
之前我从未看过唐七公子的作品,只在一些评论里,看到有人对他有如下的评价:唐七公子文风流畅,情节跌宕,擅长用幽默的语言述说令人心伤的故事,感动无数痴情男女,被誉为虐心女王。现在因为好奇所以看完了《华胥引》,果然名不虚传!在她的故事里有着接近于电影的画面感,就算这是一则古早的故事,却有着科幻小说的情节。小说里的角色与情感似古似今得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于是在阅读起来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看完了《华胥引》后,我对唐七公子本人也有了读者角度上的好奇,透过出版社的安排有机会跟她通上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子年轻而清脆的声音,完全跟我预期是一位深沉的作者不同,我特别好奇地问她是否看过《盗梦空间》这部电影,她笑着回答说:看过这篇小说的人都这么问过她,她的确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在写完这篇小说以后,这点更让我对她的想象力佩服不已。
我想也只有在笔耕的世界里的人,借由一支笔才能翱翔在这样充满了创意的空间,如同哈利・波特骑上了他那支扫帚。我衷心地期待她能继续带着喜欢她文笔的人们,往后随着她的笔不断地经历超越时空的旅行。
茶楼里的说书先生们,但凡上了点年纪的,大约都听过六十七年前发生在卫国王都里的一桩旧事。
那桩事原本是个什么模样,如今已没人说得清。但关于此事的每一段评书,不管过程如何,填充故事的因果始终如一。
因果说,卫国国君早些年得罪了陈国,四年后被陈国逮着一个机会,由陈世子苏誉挂帅亲征,直杀到卫国王城,一举大败卫国。软弱的卫王室选择臣服,卫国最小的公主叶蓁却抵死不从,盛装立在王都城墙上上斥国主、下斥三军,一番痛斥后对着王宫拜了三拜,飞身跳下百丈城墙以身殉国。
史官写史,将之称为一则传奇,更有后世帝王在史书旁御笔亲批,说卫公主叶蓁显出了卫国最后一点骨气,是烈女子。
六十七年,大晁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当年事隔得太远,百姓们遥想它,已如遥想一段传奇。而叶蓁公主的殉国之举虽感人至深,褪去神圣和风华后,却不如一段风月那样长久令人沉迷。就像在陈卫之战中,最能撩起世人兴致的,始终是她与陈世子苏誉的那段模糊纠葛,尽管谁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大晃史书对苏叶二人的牵扯有所善墨,但着墨不多,只记了件小事,说陈世子苏誉在卫国朝堂上受降时,接过卫公呈上的传世玉玺,曾提问卫公道:“听闻贵国文昌公主乃当世第一的才女,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尤其画得一手好山水,卫公曾拿这枚传世玉玺与她做比,不知本宫今日有没有这个荣幸,能请得文昌公主为本宫画一幅扇面?”文昌公主正是以身殉国的叶蓁的封号,取文德昌盛之意。
史书上记载寥寥,当年的知情人在这六十七年的世情辗转中早已化为飞灰,这桩悲壮而传奇的旧事便也跟着尘光掩埋殆尽。民间虽有传说,也不过捞个影子,且不知真假。而倘若果真要仔细打点一番这个故事,却还得倒退回去,从六十七年前那个春天开始说起。
六十七年前那个春天,江北大早,连着半年,不曾蒙老天爷恩宠落下半滴雨。大晁诸侯国之一的卫国,虽建在端河之滨,也不过饱上百姓们一口水,地里靠天吃饭的庄稼们无水可饮,全被渴死。不过两季,大卫国便山河疮痍,饿殍遍地,光景惨淡至极。
卫国国君昏庸了大半辈子,被这趟天灾一激,头一回从脂粉堆里明白过来,赶紧下令各属地大开粮仓。赈济万民。国君虽在一夕之间变做圣明公侯,可长年累下的积弊一时半会儿没法根除,开仓放粮的令旨一道一道传下去,官仓开了。粮食放了,万石的粮食一层一层辗转,到了百姓跟前只剩一口薄粥。百姓们眼巴巴望着官府赏赐的这口粥,不想这口粥果然只得一口,只够见谷玄时不至空着肚皮。
眼看活路断了,百姓们只好就地取材,揭竿而起。出师必得有名,造反的百姓顾不得君民之道,只说,上天久不施雨,乃是因卫公无德,犯了天怒,要平息苍天的怒火,必得将无德的卫公赶下王座。
谣言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一路传至王都深处,深宫里的国君被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砸得惴惴然,立时于朝堂上令诸臣子共商平反之策。众臣子深谙为官之道,三言两语耍几段花枪再道声我主英明,便算尽了各自的本分。
只有个新接替父辈衣钵的庶吉士做官做得不够火候,老实道:“都说雁回山清言宗里的惠一先生有大智慧,若能将先生请出山门,或可有兵不血刃的良策。”清言宗是卫国的国宗,为卫国祈福,护佑卫国的国运,这一代的宗主正是惠一。
大约注定那一年卫国气数将尽,卫公派使者前去国宗相请惠一的那一夜,八十二岁高龄的老宗主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谢世了。惠一辞世前留下个锦囊,锦囊中一张白纸,八个字囫囵了句大白话,说:“会盟方已,大祸东来。”卫公捧着锦囊在书房闷了一宿。房外的侍者半夜打瞌睡,朦胧里听到房中传来呜咽之声。
惠一掐算得很准,刚过九月九,一衣带水的陈国便挑了个名目大举进犯卫国。名目里说年前诸侯会盟,卫公打猎时弓箭一弯,故意射中陈侯的半片衣角,公然藐视陈侯的君威,羞辱了整个陈国。陈国十万大军携风雨之势来,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不到两个月,已经列阵在卫国王城之外。
全天下看这场仗犹如看一场笑话,陈侯手下几个不正经的幕僚甚至背地里设了赌局,赌那昏庸的老卫公还能撑得住几时。陈世子苏誉正巧路过,押了枚白玉扇坠儿,摇着扇子道:“至多明日午时罢。”
次日正午,懒洋洋的日头窝在云层后,只露出一圈白光,卫国国都犹如一只半悬在空中的蟋蟀罐子。
午时三刻,白色的降旗果然自城头缓缓升起,自大晁皇帝封赐以来,福泽绵延八十六载的卫国,终于在这一年寿终正寝。老国君亲自将苏誉迎入宫中,朝堂上大大小小的宗亲臣属跪了一屋子,都是些圣贤书读得好的臣子,明白时移事易,良禽该当择木而栖。
午后,日头整个隐入云层,一丝光也见不着,久旱的老天爷却仿佛一下子开眼,突然洒了几颗雨。陈世子苏誉身着鹤氅裘,手中一枚十二骨纸扇,翩翩然立在朝堂的王座旁,对着呈上国玺的老国君讨文昌公主扇面的一席话,一字一句,同史书记载殊无二致。
不过,苏誉并未求得叶蓁的墨宝,他在卫国的朝堂上对卫公说出那句话时,叶蓁已踏上王城的高墙。苏誉和叶蓁有史可循的第一次相见,在卫国灭亡的那个下午,中间隔着半截生死,百丈高墙。
他甚至来不及看清传闻中的叶蓁长了如何的模样,尽管他听说她为时已久。听说她落地百天时,卫公夜里做梦梦到个疯疯癫癫的长门僧,长门僧断言她虽身在公侯家,却是个命薄的没福之人,王宫里戾气太重,若在此扶养,定然活不过十六岁。
听说卫公听信了长门僧的话,将她自小托在卫国国宗抚养,为了保她平安,发誓十六岁前永不见她。还听说两年前卫公大寿,她作了幅《山居图》呈上给父亲祝寿,列席宾客无不赞叹,卫公大喜。
细雨蒙蒙,苏誉站在城楼下摇起折扇,蓦然想起临出征前王妹苏仪的一番话:“传闻卫国的文昌公主长得好,学识也好,是个妙人,哥哥此次出征,旗开得胜时何不将那文昌公主也一道迎回家中,做妹妹的嫂子?”城墙上叶蓁曳地的衣袖在风中摇摆,那纤弱的身影突然毫无预兆地踏入虚空,一路急速坠下,像一只白色的大鸟,落地时,白的衣裳,红的血。城楼下的卫国将士痛哭失声。
苏誉看着不远处那摊血,良久,合上扇子淡淡道:
“以公主之礼,厚葬了罢。”
四月,山中春光大好,消失六个月的君师父终于从山外归来。这意味着,我的前肢和躯干不久就可以拆线了。
六个月来,我一直保持全身缠满纱布的身姿,起初还有兴致晚上飘出去惊吓同门,但不久发现被惊吓过一次的同门们普遍难以再被惊吓一次,而我很难判断哪些同门是曾经已被惊吓过的,哪些没有,这直接导致了此项娱乐的命中率越来越低,渐渐便令我失去兴致。
两个月后,我已经有些受不了了。
很多同门以为我是受不了每天缠着纱布去药桶里泡四个时辰,其实不然,泡澡有益身心,只是泡完之后还要裹着湿答答的纱布等待它自然晾干,令人痛苦非常。这种痛苦随着大气温度的降低而成反比例增长。
后来,我想,所有不世出的英雄们在成为英雄的过程中,总是受到他们师父别出心裁的栽培,君师父必是借此锤炼我的毅力和决心,想通此处,即使户外结冰的寒冬腊月,我也咬牙坚持,且从不轻言放弃,哪怕因此伤寒。
坚持了半年,经过反复感染伤寒,我的抗伤寒能力果然得到大幅提升,和君师父一说,他略一思索,回答:“啊……我忘了告诉你澡堂旁边有个火炉可以把你身上的纱布烤烤干了,哈哈哈……”
君师父是君禹教宗主。君禹教得名于君禹山,君禹山在陈国境内。据说开山立教的祖宗并不姓君,而是姓王,出身穷苦,父母起名王小二。
后来王小二祖宗从高人习武,学成后在君禹山上立教,但总是招不到好徒弟,一打听才知道,别人一听说君禹教宗主叫王小二,纷纷以为这是个客栈伙计培训班,招的徒弟学成以后将输送往全国各地客栈从事服务行业。
王小二祖宗迫于无奈,只好请了个附近的教书先生帮他改名,教书先生纵观天下大势,表示慕容、上官、南宫、北堂、东方、西门等大姓均已有教,东郭和南郭这两个姓虽然还没立教,但容易对品牌造成稀释,效果就跟大白鹅麻糖怎么也干不过大白兔麻糖一样,倒不如就地取材,跟着君禹山,就姓君,也可以创造一个复姓,姓君禹。
但考虑创建复姓要去官府备案,手续复杂,不予推荐,还是姓君最好,而且君这个姓一听就很君子,很有气质。王小二一听,心花怒放,从此便改姓君,并听从教书先生建议,将小二两字照古言直译了一下,少双,全名君少双。
王小二化名君少双后,果然招收到大批好弟子,从此将君禹教发扬光大。君师父正是开山祖师君少双的第七代后人。
我从小就认识君师父,那时我还生活在卫国的国宗――清言宗里,我此生的第一任师父――惠一先生也还活得好好的,牙好胃口好,连炒胡豆都咬得动。君师父就带着他儿子住在清言宗外,距雁回山山顶两里处的一间茅草棚中,常来找我师父下棋。
师父带我去山顶看日出时,也会在他的茅棚叨扰一宿。他们家只有一张床,每次我和师父前去叨扰,总是我一个人睡床,他们仨全打地铺。这让我特别喜欢到他们家叨扰,因为此时,我是很不同的。
后来,我将自己这个想法告诉了君玮,君玮就是君师父的儿子。君玮说:“可见你骨子里就该是一位公主,只有公主才喜欢与众不同。”但我不能苟同他这个见解,公主不是喜欢与众不同,而是习惯与众不同,最主要的是没有人敢和公主雷同。而习惯和喜欢之间,实在相差太远,这一点在我多年后临死之前,有很深刻的体会。
君玮其实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人,他精通历朝历代每一个皇帝的所有小老婆,甚至包括微服私访时有了一夜情却没来得及娶回去的。
君玮的看法是,家事影响国事,国事就是天下事,而皇帝的家事,基本上都是小老婆们搞出来的事。其实只要皇帝不娶小老婆那就没事,但这对一个皇帝来说实在太残忍,皇帝觉得不能对自己这么残忍,于是选择了对天下人残忍。
君玮的思路是,和谐了皇帝的小老婆们,就是和谐了全天下,此后,他一生都致力于如何和谐皇帝的小老婆。
除了这件一生的事业,君玮还有一个兴趣,那就是写小说。但这个兴趣让君师父很不齿,君师父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享誉一方的剑客,只要他一写小说,就会没收他的稿纸并罚他抄写剑谱,于是他只好把文学和武学结合在一起,在抄写剑谱的过程中进行小说创作。
你会发现经君玮抄过的剑谱总是大为走形,比如他写:“每日阳时,她用一双素手脱去一层一层繁复的衣衫,将净瓷般的身体裸露在日光下。那是一处极寒的所在,她坐在一张泛着冷光的寒冰床上,冷,很冷,非常冷,她就那么盘腿坐着,面北背南,将气息运行圆满的一周。她不知道,十丈远的重重冬蔷薇后,正有一双漆黑的眼睛,一寸一寸地抚摸她的肌肤。”
基本上没人想得到这其实是四句剑谱心法“极寒阳时正,独坐寒冰床,裸体面朝北,气行内周寰”。后来,君玮成为了小说写得最好的剑客和剑术最高强的小说家。
我因独自长在清言宗,宗里的规定是男人不得留发,全宗两千来号人,除了我以外全是男人,导致整个清言宗只有我一个人留长头发。
这让我在初具性别意识时,很长时间内都以为女人和男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女人有头发而男人们全是秃头。于是,理所当然,我认为君师父和君玮都是女人,出于同性的惺惺相惜之感,和他们走得很近。
很自然的是,后来我终于明白他们父子俩都是男人,但那种想法已根深蒂固,导致此生我再也无法用男女交往的心态面对君玮,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姐妹,故事本该是青梅竹马,却被我扭转成了青梅青梅。
三岁时,我在偶然的机缘下得知自己是卫国公主,但对这件事反应平静。主要是以我的智慧,当时根本不知道公主是什么东西。君玮比我大一岁,知道得多些,他说:“所谓公主,其实就是一种特权阶层。”我问:“特权是什么?”君玮说:“就是你想做的事就可以做,不想做的事就可以不做。”听了他的话,当天中午我没有洗碗,晚上也没有洗衣服,结果被师父罚在祠堂里跪到半夜。
从此以后,我彻底忘记了自己是公主这件事。也就是在同一年,师父看我心智已开,正式着手教我琴棋书画。师父的意思是,人生在世,能有个东西寄托情怀总是好的。
如果我能够样样精通,自然最好,算是把我培养成了大家;如果只通其中一样,那也不错,至少是个专家;如果一窍不通,都知道一点,起码是个杂家。我问师父:“万一将来我不仅不通,还要怀疑学习这些东西的意义呢?”师父沉吟道:“哲学家,好歹也是个家……”
不知为什么,君玮明明没有拜师父为师,却能跟随我一同学习。师父的官方解释是,学术是没有国界不分师门的,君玮私下给我的解释是,他爹送了师父十棵千年老人参。
果然,学术是无国界的,国界是可以被收买的。和君玮一起上课,写字画画还能忍受,但弹琴时就很难受。初学琴时,我和君玮一人一张琴,分坐琴室两端对弹。直接后果是,在我还不懂得何为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年纪里,首先明白了何为魔音贯耳腐骨蚀魂。
我们彼此觉得对方弹得奇烂无比,令自己非常痛苦,并致力于制造出更加匪夷所思的声音好让对方加倍痛苦,以此报复。在我的印象中,琴是凶器,不是乐器。这也是为什么我学会了用琴杀人,却始终学不会用琴救人,完全是君玮留给我的心理阴影。而在我学会杀人之后,想要依靠我的琴音得救的人,全部死去了。我在十岁的时候捡到一只刚睁眼的虎崽,这只老虎跟随了我一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一头禽兽的忠诚。虽然回想当年,我和君玮捡它的本意不过是为了把它吃掉。那时正遇上君玮他爹被我师父说动,立志做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并身体力行,搞得君玮三月不知肉味,而我在国宗里鲜少吃肉,正是我们俩对肉最向往的时节。
后来之所以没吃成,完全是因为我们觉得还可以把它再养大一点,这样就能既蒸又煮连炖带炒,说不定还有剩。现在想来,能够忍住欲望没有当场宰掉小黄烤烤吃了,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小黄正是这头老虎的名字,后来经过鉴定,发现它所属的虎种相当名贵。我和君玮都很高兴,觉得可以把它卖掉,这样我们就发财了,但苦于找不到门路,只好不了了之。
等到我们有门路的时候,都已成年,最主要的是纷纷变成了有钱人,不用再拿小黄换钱。这让我们十分感叹,人生大抵如此,发财的道路总是艰辛。
命运安排我每次遇上大事时总是孤身一人,并且必然受伤。师父说:“你听过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伤筋动骨……”我能想象上天降到我身上最大的任莫过于等师父死后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下一任宗主,但后来君玮把宗规偷出来给我看,宗规里明文规定了女人及人妖均不得在国宗内担任要职,从而破灭了我的一个梦想。
很多人在梦想破灭之后迅速堕入歧途,山下就有个刺客因业绩不好而退隐江湖,改行杀猪,还有个书生在科举落第后改写淫秽小说并兼职画春宫图。但我始终认为做梦和娶妻性质差不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并且新的往往比旧的更好,旧梦破碎是因为新梦想即将到来,而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断然没有理由消沉。
我对君玮表达这个看法,君玮思索一阵,认为有理,下午便去山下安慰刚死了老婆的王木匠,道:“你老婆死了是因为即将有新老婆来嫁给你,新老婆肯定比你旧老婆好,这是件大喜事啊,你表现得高兴点,别这么伤心。”被王木匠挥舞着扫把撵了半条街。君玮不能理解,且有些受伤,我安慰他:“世人都习惯在真相面前表露出狰狞的一面,以掩藏心的羞涩。”
在宗主梦破灭的那个夜晚,我的做法是,日暮时晃出宗门,前去林中打坐打鸽子,转换心情,寻找灵感,建立新的梦想,重树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实在要算一个积极向上之人。
除此之外,这种积极还表现在一些私生活上,比如我一直毫不怀疑,倘若日后自己有一个夫君,他又不幸死在前头,我势必会在他断气当夜就收拾行装出门,前去大千世界寻找新的夫君。
而截至那个夜晚,我受君师父感染,习惯性以为自己将来的夫君必然就是君玮,常常看着活蹦乱跳的他无限忧虑,想着:啊呀,我怎么能在面前这个人刚刚断气时就马上出门寻找第二春啊?
好在该想法只持续到我十四岁时、打算重塑梦想的这个仲夏夜。
关于仲夏夜,有一切美好的词汇可以形容,最切实的说法却往往残忍。据说仲夏夜时毒蛇凶猛,宗里已有三名弟子因在此时节外出而死于蛇祸,望各位弟子引以为戒,各自珍重。
我年纪幼小,总相信自己很特别,断不会重蹈那三个倒霉蛋的覆辙,这趟外出便没有携带雄黄,如今想来,当年死于蛇口的那三个师兄必然也以为自己很特别。人人都以为自己特别,看在他人眼中却无甚特别,看在蛇的眼中就更不特别了。
估计对于毒蛇们来说,只有带了雄黄的人才特别。幼时我们总是追求和他人的不同之处,长大却总是追求和他人的共同之处,如果能反过来一下,岂不正好,至少三位师兄的三条小命说不定能就此保住,哪怕成为植物人。而作为同样不带雄黄的人,显然毒蛇对我是很一视同仁的。
一尾娇小的白唇竹叶青狠狠在我小腿上咬了一口,毒液通过血液循环往身体各处。我摇晃了一会儿,缓缓倾倒,意识模糊之际,终于领悟了本段落前半部分陈述的道理。接着还回忆了一下那幅画了两天的山中古寺图是否已裱好,回忆完之后觉得生无可恋,可以安息,遂安详地闭上眼睛等死,并再也睁不开了。
就在那时,鞋子倾轧过落叶枯枝的微响由远及近,停在我的身边,一双手臂将我凌空抱起,鼻尖传来清冷梅香,可想象星光璀璨,静夜无声,满山盈谷的,那是二月岭上梅花开。
我醒来时感觉身体内部血液涌动,齐向下腹聚集,手抚上裹肚,阵阵温痛。脚踝处被蛇咬的地方麻木不仁,却贴着一个温软物体,而膝盖弯曲,小腿被某样东西凌空支起,像一根绷紧的皮绳。整体感觉如此古怪,我忍不住要睁开眼睛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睁眼偏头,却看见要命的场景。环境是山洞一个,石床一张,我躺在这张石床上,而白色月光下,右脚小腿正被一个男人紧紧握在手中。
他手指修长莹白,从姿势及触感辨别,脚踝处伤口紧贴的正是他的嘴。我的角度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且这侧面还大部分被头发挡住,令人很有一撩他头发的冲动。他没有发现我醒来,一身玄青衣衫,只静静坐在石床侧沿,唇贴着我的脚踝,宽长的袖摆沿着他抬起的我的小腿一路滑下,低头能瞥见衣袖上繁复的同色花纹。
周围物什全都失色,朦胧不可细看,他漆黑的发丝扫过我的脚背。可想如果不是这样的场景,一位曼妙少女和一位翩翩公子的相遇,该是像书法大家的草书一样行云流水。而很自然的是,我自以为被人轻薄,顺势便给了他一脚。这一脚踢得太用力,引起连锁反应,身体某个难以言说的部位顿时血流如注。
我和他第一次相见,踢了他一脚,结果踢出我的初潮。
他自然没有被踢到,在我右脚猛然发力前已不动声色后退一步,可见他的身手了得。而我完全没发现他到底是怎么突然从坐姿变为了站姿,可见他的身手着实了得。我眯着眼睛看他,在洞口照进的白月光中,他身姿高大挺拔,一枚银色面具从鼻梁上方将半张脸齐额遮住,面具之下嘴唇凉薄,下颌弧线美好。
有片刻的寂静。
他擦拭掉唇上残留的血痕,唇角微微上翘:“好厉害的丫头,我救了你,你倒恩将仇报。”
但我被身体的大规模出血惊吓,不能说出什么解释的话,张口便是一阵哇哇大哭,并且在哭泣的过程中,过度使用小腹运气,导致下身渐渐有血污渗透裙子,一层漫过一层,越染越严重。而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那天我穿的是一条白裙子。他的视线渐渐集中在我的裙子上,顿了半天,道:“葵水?”
我抽泣说:“谢谢,我不渴,但我可能是得了败血症,马上就要死了。”
他继续关注了会儿我的裙子,咳了一声:
“你不会死的,你只是来葵水罢了。”
我大为不解:“来葵水是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这件事本该你母亲告诉你。”
我说:“哥哥,我没有母亲,你告诉我。”
很难想象,我会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男人身上获得关于葵水的全部知识。但更加难以想象倘若由师父他老人家亲口告诉我“所谓葵水,就是指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子宫出血……”会是什么模样。连苍天都觉得这太难为一个七十九岁的老人家,不得不假他人之口。
他说他叫慕言。当然这不会是他的真名。假如一个人脸上戴着面具,名字必然也要带上面具,否则就失去了把脸藏起来的意义。
而我告诉他我叫君富贵,则纯粹是担心这人万一是我那从没见过面的爹的仇人,一旦得知我是我爹的女儿,一怒之下将杀人泄愤。历史上有诸多例子,表明很多公主都曾被他们的老子连累送命,再不济也会被连累得嫁一个和想象出入甚大的丈夫,导致一生婚姻不幸。
就这样,我们在山洞里待了四五天,喝的水是洞外的山泉,吃的东西是山泉里野生的各种鱼类。据说我不能立刻回去,因为毒还没有解完,而慕言表示,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半途而废不是他的风格。
我每天需要吃一种药,然后从手腕入刀割个口子,放半杯血。当我放血的时候,慕言一般坐在床前的石案旁抚琴。琴是七弦琴,蚕丝做的弦,拨出饱满的调子,具有镇痛功能。每次慕言弹琴,我总会想起君玮,还有他那令人一听就简直不愿继续在世上苟活的弹琴水平,进而遗憾不能让他来听听面前这位奏出的天籁之音,好叫他羞愤自杀,再也不能贻害世人。
五天里,我一直很想把慕言脸上的面具扒掉,看看面具底下的脸到底长什么样,但一想到结果可能被他砍死,实在不敢轻易造次。这完全是人的好奇心作祟,有时候有些事根本不关你的事,却非要弄一个明白,真是没事找事。
第六天下午,我觉得脚伤已好得差不多,能够直立行走了。慕言端详了会儿我的伤口,道:“不用继续放血了。明日一早我便送你回去吧。”
没想到分别来得这样迅捷,关键是还没成功扒开他的面具,我一时接受不了,残念地愣在那里。
他说:“不想走?”
我摇头说:“没有没有,但是,哥哥,你不和我一起走么?这个山洞没有太多东西,你也不像是要在此处久居。”
他沉吟说:“我不走,我得留在这里。”
我说:“可你留在这里做什么呢?你一个人,没有人陪你聊天,也没有人听你弹琴。”
他低头拨琴弦:“等人,我怕我走了,我要等的人就找不到我了。”
我顿时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再问下去仿佛已涉及他人隐私,不问下去又一时找不到话题转移。我说:“这个……”
他已从石案前站了起来,笑道:“说到就到,今天可真是运气。”
我抬头看,高阔的山洞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站了一堆蒙面的黑衣人。在我看向他们的一刹那,这些人纷纷亮出自己的兵器。拔兵器的动作就像他们的服装一样统一,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纪律的团队,而难得的是,拔出的兵器也很统一,明晃晃一把把镰刀排得很整齐。